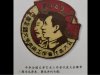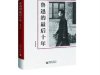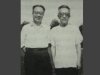;联系游戏”,最后得出了结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我们听完,似懂非懂,仿佛学到了一点什么,又仿佛什么也没听到,总之是记住了这样一句可以今后写到作文里的“哲学”真理:“事物是普遍联系的”。
就这样,我的“高中政治”就停留在了这么一个“拾人牙慧”的二把刀水平。至于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什么坚持党的领导、为人民服务,再什么依法治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虽然也能装模作样地捣鼓点官腔官调,偶尔也能整些“基本方略”“根本保证”这样的官样文章,但和文科同学的差距在于,我没法记住究竟“坚持党的领导”是“基本方略”,抑或“依法治国”是“根本保证”?
然而,若说我的“政治知识”仅止于此,那也未免是个过快的论断。事实上,一方面是受了父亲每天24小时循环播放新闻广播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想在同学面前展现“关心国家大事”的正面形象的虚荣心理作祟,我确然是从很小就有兴趣听些社会新闻和政治评论的。东听听西听听,不免就学到些不明觉厉的词儿,其中既有“街头政治”这样令人似懂非懂的,又有“网络小说”这样时髦的,再有“比特币”这样听来高大上的。学到了词儿就爱和人炫耀,就爱侃大山,以至于在博客刚刚开始流行的时候我就敢从“街头政治僵局”一路写道“比特币的失败”。当然,个中观点也都是移花接木的东拼西凑。不过,要说这些随处听来的观点里是否是有些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呢?在写这篇回忆前我还特地翻来找找,结论是即使是有些影响,但也绝不明显。想来当时也正值中文互联网作为公共空间的鼎盛时期,自由派大行其道,左派和建制派是在哪里都要挨打的。这样一说,或许今天的我也就是深受当时的“公知自由派”荼毒的孽种吧。
有趣的是,尽管在当时我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几乎是零,对社会问题的分析在今天看来也幼稚的可笑,但我的几篇“评论”却在结尾上有着令人哭笑不得的巧合:“所以,中国的教育改革,任重而道远,要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实现教育公平,防止中国的人才继续向发达国家流失,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只有如此,才能进一步建设更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2];“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也是一个值得发人深省的问题,如果社会的接班人都思想腐化,没有正确的价值观,我们的社会将变成怎样,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3]。哈哈,一个对于马克思主义毫无了解的毛头小子,竟然在对所有社会问题的长篇大论后都要拿“社会主义”为自己的立论背书!
当时的奇妙心理,我已是回忆不起来了。直到我看到余华谈到他和鲁迅的故事时,我才明白对于这样一个未涉世事的小子来说,“社会主义”这样的名字意味着什么。由于余华的这段文字是如此精彩,以至于我认为任何的缩写、概括都会尚还故事的完整性,因此我把它完整地附在了文末。而我想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每个人童年时期对于“社会主义”或“鲁迅”这样宏大概念的第一印象,或许都大抵如此吧。
二
某个水果店经理在洋葱、胡萝卜陈列橱窗上贴了一幅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这样做目的何在?究竟向人们传送什么信息?他是否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大联合真的十分热衷?他当真觉得他的热情促使他非得让公众都来了解他的理想不可?他是否真的想过,这个大联合该怎么实现,实现了又怎么样?我敢断言,大多数商店经理们对于橱窗上标语的意义从来是不会过问的。他们也不会用那样的标语来表达自己真实的意见。标语是上面批发洋葱和胡萝卜的同时发下来的。水果店经理拿过来往橱窗上一贴就完事了,因为这是习以为常,司空习惯的事情。但要是不贴,就会有麻烦。上面会指责他不按规定布置橱窗,有人甚至会控告他反党反社会主义。为了过得下去,他非照章办事不可。这样的小事千千万万,做了才能有过上“与社会谐调一致”的生活保障。——【捷】瓦茨拉夫·哈维尔:“无权者的权力——纪念扬·巴托契卡”,1978年
如果仅仅根据一个中国学生在学校里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来判断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那未免有些过于天真了。即使是一个从来没有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至少在他每天打开电视机的时候会习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