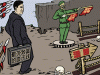游击战期间,部分是因为艰苦的物质条件,绝大多数游击队员都蓄起了胡须,菲德尔和其他领导人在西方媒体上的形象就是如此。久而久之,胡须似乎就成了菲德尔和他的追随者的形象特征。巴蒂斯塔政权垮台,游击队从山上下来时,黑色长胡须(或者络腮胡须)、橄榄绿军装和美式步枪成了革命者的"标配"。为了维持这个特殊的群体形象,菲德尔明确要求不准剃胡子。留胡须的游击队员(guerrilla-barbudo)或简称"胡须汉"(barbudo)拥有地位和特权,乘坐公交车、进电影院免票,因为他们名义上不领工资。革命后的哈瓦那蓄胡不但"政治正确"而且引领时尚,男人们纷纷仿效,市面上美国产剃须刀销量大跌。
但是佛兰基一进哈瓦那就找了个理发匠剃掉了胡子。菲德尔到了哈瓦那第一次看见他时吃了一惊,质问道:"你怎么会弄掉胡子的?"佛兰基说:"理发匠帮我剃的。"菲德尔说;"这怎么行?胡子是革命的象征。它不属于你个人。它属于革命。"佛兰基说:"哈瓦那太热了,再说我的孩子会认不出我,我做爱时也嫌长胡子碍事。别忘了我是个平民,不是军人。"菲德尔仍然摇头说:"我仍然搞不明白你怎么可以剪掉胡子,真搞不明白,你这个蠢驴。"佛兰基说:"菲德尔,胡子毕竟是我自己的,对吧?"菲德尔说:"不,不。我不允许这里的任何人剃掉胡子。"佛兰基说:"我可以保证,将来这里只有一个人会一直留着长胡子,那就是你自己。不信打个赌?"
佛兰基说这话半个多世纪以后,一直到去世,菲德尔都留着他那象征古巴革命的一把大胡子,而绝大多数游击队出身的领导人包括劳尔不久就都剃掉了胡子(尽管他的胡子远不如乃兄)。
4道成肉身—看穿个人崇拜的本质
那么,胡子的象征性仅在于革命吗?彼得大帝发动欧化改革时曾经视俄国人留长胡子为陋习,颁布"剃胡令",但俄国人视胡子为东正教文化的一部分,因为圣像上的耶稣和后来的多数圣徒都是留胡子的,所以很多人抗拒,彼得规定不服从的起码要为胡子付税。作为天主教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家,古巴革命在心理深层其实很有或明或暗的宗教情结。卡斯特罗兄弟少年时都是在古巴最严格的耶稣会学校当住宿生的,深受天主教文化熏陶(古巴革命后期他们都和罗马天主教会妥协,甚至规定党员可以信教)。佛兰基说他不服从菲德尔的"蓄胡令"就是不想让自己看上去像个圣像上走下来的圣徒。
菲德尔当初乘坐"格拉玛"号从墨西哥回到古巴时,队伍被政府军打散,只有十二个人跟他上了马埃特腊山,正好暗合了耶稣基督和十二个门徒的典故。这个暗合在古巴的广泛流传从来就是受到菲德尔默许的。佛兰基甚至说菲德尔视自己为革命的"三位一体"—"七·二六运动"(象征是红色与黑色)、游击队(象征色是橄榄绿)和他本人。三位一体是天主教概念,即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个位格都体现神性。和菲德尔有关的一个近似神迹的现象也受到官媒的渲染:在革命胜利初期,菲德尔好几次在公共场合露面或发表演说时(包括一次访问美国在纽约街头),都有鸽子从天而降,栖息在他的肩膀上,引起围观群众如痴如醉的欢呼。
佛兰基观察到,从巴蒂斯塔垮台到菲德尔进入哈瓦那有一周时间,菲德尔不让任何重要的游击队领导人如格瓦拉先期入城,尽管后者的队伍就在哈瓦那城下,而是等自己从古巴岛的东端游击队大本营所在地长途进军,一路上像先知被信众环绕一样接受群众的欢呼并到处发表演说,最后在万众欢腾的高潮中进入哈瓦那。佛兰基说,这正像圣经中说的"太初有言,言与神同在"(中文一般译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里用"言"以契合本文的语境。圣经英文版中就是大写的"Word"。)。
从1959年初开始,尤其是在六十年代,菲德尔在群众集会上发表了难以计数的现场演讲,通过古巴革命前就建立的先进的无线电和电视网络向全国转播。这些演讲动不动就是六、七个小时甚至更长,腔调激进而武断,完全不再像是那个马埃特腊山上清醒理性的反对派领导人,而是一个教长甚至先知,然后其文本又将报刊的版面几乎全部占满。
这些巨量的话语和他无处不在的形象、视察和指导(佛兰基说这就是所谓神的"全在")将菲德尔的个人存在极度放大,充分占据了民众的听觉、视觉甚至想象空间,不但等同于革命,所谓道成肉身(本人就是革命的化身),而且逐步使得很多古巴人把他的存在作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菲德尔"、"革命"和"生活"三个概念在古巴几乎成了同义词。
今天回首二十世纪的革命,个人崇拜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在不同的国家,个人崇拜有不同的形式,很多都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而所谓宗教色彩其意义是很广泛的,但其核心不外乎都是道成肉身。很多人说古巴没有个人崇拜,这是用其他国家的形式去套,好像只有喊万岁才算。对这个问题缺乏认识甚至意识,就会把制造出来的个人崇拜当作是自发的大众支持,不但陷入概念误区,而且曲解革命的历史。佛兰基的观察在这个意义上对祛魅很有启发。他对鸽子落在肩膀上这个似乎不可思议的现象的嘲弄就是如此,他说或许那些鸽子只是找到了一个非常方便落粪的地方。
个人崇拜也有比道成肉身更世俗更现实的一面,就是盲目相信领袖万能,类似求神拜菩萨。革命前的古巴金融、商业、地产业和服务业高度发达,革命后政府手里接管了巨量的物质财富,为了赢得大众的支持便随意挥洒,降低房租和消费品物价,开放海滩和服务业,一方面提高工资,另一方面还免费提供很多公共服务,城市贫民和下层民众一片欢呼。菲德尔走到哪里,都会被群众围绕,向他要这要那。佛兰基说他们给菲德尔起了个"马"的外号。"马"是古巴华人社区博彩业中的幸运号码,得了就是大满贯。以此称呼菲德尔,意为有了他什么都有了。对这个外号,菲德尔一开始很不高兴,后来也就默认了。法国哲学家萨特1961年初访问古巴时看到这个情形,又兴奋又担心地问菲德尔:"要是他们向你要月亮怎么办?"
5不当政府部长,宁愿独立办报
革命初期佛兰基和菲德尔的另一次冲突是关于佛兰基的工作安排。巴蒂斯塔垮台的消息传出时,菲德尔不在总部,所以佛兰基通过"起义之声"发布了一些临时指令,菲德尔都认可了。当他向哈瓦那进军的途中,一路上忙于发布人事任命,接管旧政权。
当他遇见佛兰基时他说:你知道我的想法,你来当劳工部长吧。佛兰基用玩笑回答说如果劳工部长的任务就是在工厂建立社会主义,让工人来管理,那我可以。菲德尔又说:"那你来做财政部长怎么样?"佛兰基说那更是离谱。他说自己在西方和拉美文化界有很多朋友,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得支持,在古巴发动一场文化改造和文化复兴。但菲德尔认为文化工作完全不是当务之急。
这个插曲让我想起了十月革命时列宁把机关枪手派去接管国家银行的故事。佛兰基说,菲德尔认为自己了解他的想法,这就够了,所以任命自己做部长,但实际上没人了解他的想法。他从来不告诉别人他的想法,他没有这样的习惯。他只告诉别人他的决定。这既有可能是菲德尔自己当时确实对突然降临的管理国家的责任毫无准备,也有可能是他驾驭部下控制局面的权术手段。
对菲德尔任命的拒绝让佛兰基再一次面对革命胜利后的那个困境:为了推翻巴蒂斯塔,是不是只有接受菲德尔?在这个问题没有答案的时候,他只能对自己说:我参加斗争可不是为了到了胜利的时候再退出。他决定继续观察菲德尔,采取"既在革命之中又和革命保持距离"的立场,通过办报纸继续发挥自己的影响。回到哈瓦那,他就恢复了被巴蒂斯塔取缔的"革命报"。
"革命报"虽然和"七·二六"运动有历史关系,但它的恢复不是菲德尔的授意。由于"七·二六"运动没有自己的出版物,所以在一段时间里,"革命报"就成了革命舆论的主要喉舌。菲德尔对它是既利用又观察,而佛兰基的原则是既不完全听命于菲德尔又不过分忤逆他的意志。
6"星期一"周刊与短暂的文化自由
除了政治新闻,佛兰基为"革命报"创办了一份名为"星期一"的文化周刊,宗旨是贯彻古巴民族主义之父何塞·马蒂"文化带来自由"的思想,提升古巴民族的文化水平。"星期一"大量发表西方和拉美文化名人如萨特、福克纳、毕加索、米罗(Joan Miró i Ferrà,西班牙著名画家和雕塑家)、伍尔芙、布莱希特、博尔赫斯、聂鲁达等人的言论和作品,甚至包括托洛茨基和帕斯特尔纳克的作品,同时发表反映古巴社会变迁中复杂现象的深度报道。
在形式上,佛兰基想把"星期一"办成不同于传统报纸而更像是现代都市媒体的图文并茂的大型刊物,在版面安排和视觉上追求冲击性效果,借用西方新兴的未来主义、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形式,甚至字母的样式和句子的排列都别具一格。由于这份周刊聚集了古巴最有影响的作者群,它体现了古巴文化知识界革命后的动向和追求,似乎成了他们的思想文化阵地,发行量达到二十多万份。后来,佛兰基还以这份刊物的方针和内容为基础开办了一个电视新闻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