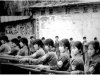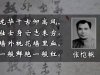理论研究不是设计政治方案。政治设计可以有步骤,有妥协,有过渡。因为各个政治主体的立场不同,力量强弱也不同,彼此的诉求都不相同,要找到一个结合点十分不易,很难痛痛快快,常常是拖泥带水。这需要政治家的智慧和技巧。讲理论就要抛开一切利害得失,剥去所有外衣和偶然因素,把问题说透。讲理论只问真不真,不必考虑谁看了会怎样,尤其不能考虑当权者看了会怎样。事实上你即使想打动当权者,也是把问题说得越透,越有可能打动他的心。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我曾有短暂的时间活跃于理论界,这也是我这一生中仅有的几年,此后即销声匿迹。虽然在闲暇时曾写了两本书(一本自传,一本历史)在海外出版,但都没有任何影响。这是因为那些书都是“向后看”而没有“向前看”,所以远离万众瞩目的现实焦点。其实我的写作即使紧叩当前政治风云,也不会有多大作用,因为我的读者在国内,而我的著作已不能和国内的读者见面。
其实平心静气想想,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在理论园地里耕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需要,也总能涌现出它所需要的人才。封锁资源,箝制思想,固然会扼杀人才,但也会磨练出人才。在网上和书报刊物上,经常可以看到犀利的政治评论,深刻的思想探讨,以及资料丰富功底扎实的理论研究。它们的作者当中也有“宿儒”,但更多的是后起之秀,这正是理论界的希望之所在。
面对理论园地的新气象,我得老老实实承认:自己的知识结构,以及对现实的观察和分析能力,已经大大落后了。所以这些年已经不大写什么东西。偶尔和友人相聚,除了翻翻陈年老账之外,也谈不出什么新的见解。虽然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有些新的想法,但是由于功底不深,讲不出多少道理。去年座谈谢韬文章时随便说了几句,不料被贴到网上,有的地方还不太准确。既然如此,索性结合个人理论活动的经历,把那些粗浅的想法写出来,算是对自己的“思想史”作个反省吧。
原载《往事》第七十一期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出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