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OpenAI首席技术官 Mira Murati回到母校参加访谈,一句话惹了众怒。
一些创造性的工作可能会消失,但也许它们本就不该存在。
网友们生气的原因在于,她无差别扫射了创意产业。被 AI抢走饭碗更彻底的否定是,在座的各位人类压根没有上牌桌的价值。
别急,其实 Mira还紧接着说了:“如果产出的内容质量不高的话。”这话听起来容易接受了,优胜劣汰,愿赌服输,自古皆然。

然而,搞技术的 Mira还是无法预测市场,人类未必输在质量上。
现在很多创意从业者的处境是,被“便宜大碗”的 AI抢占了工位,给 AI生成的垃圾“去 AI味”。
为 AI打工,直到失业
写手 Benjamin Miller,是其中一位为 AI打工的人类。
他的前司负责给一家从事房地产、二手车行业的科技公司写宣传稿,他算得上是一个部门小领导,手下有60多名写手和编辑。
2023年的一天,公司为了用 AI降低成本,推出了一套自动化工作流:上级把文章标题插入在线表格,AI根据标题生成大纲,写手们不必有自己的想法,围绕大纲创作文章就好。
Miller负责的,是整个系统的末端,在文章发表前进行最后的编辑。
系统还在升级。几个月后,大部分写手被辞退,因为公司的想法又变了——ChatGPT可以直接写完整篇文章,何苦由人类做中间商。
留下来的少部分员工被迫变了工种,负责给 AI生成内容加点“人味”。
删减、修改错误、去掉过于正式或者热情的语言......对于 Miller来说,为 AI写手收拾烂摊子的工作量比人类写手多,同时又很重复和无聊,“我开始觉得我是机器人”。
人和 AI的位置悄然倒转:AI负责创新,人类负责重复劳动。
公司裁人上了瘾,2023年初,团队还有几十名作者和编辑,到了2024年,只剩下 Miller一个人,每天睁眼闭眼就是打开文档修改 AI生成的文字,再到4月,他也被公司辞退——这个系统已经不需要人了。
写手 Catrina Cowart也做过类似的工作,但和 Miller不太一样,除了乏味,她还觉得“麻烦”和“可怕”。
让 AI读起来更“像人”,并不是简单的校对,而是要对整篇文章深入编辑。
删掉 therefore(因此)、nevertheless(尽管如此)等不适合日常的华丽词藻,只是 Cowart的一小部分工作。
同时,因为 AI会编造虚假信息,Cowart还要反复核实事实,除了显而易见的错误,AI也会在那些不起眼的地方掉链子,让人防不胜防。
这个过程比从头写文章还费时,但因为 AI已经提前“写”好了内容,Cowart的工作从“原创作者”降格成了“AI编辑”,接单平台提供的工资比以前更低了——从每个单词最多10美分,到每个单词1到5美分。
AI比人类省钱很好理解,但为什么要花费额外的功夫,给 AI内容加点“人味”?
除了改善质量,让阅读体验更好、被搜索引擎抓取,这也是一个额外的商机。

一些写手专门负责一件事:修改 AI生成的内容,摸索怎么不触发 AI检测器,为反检测 AI模型和软件出一份力,最终让频繁使用 AI的内容创作者们为这些产品买单。
其中一个反检测 AI工具提出的口号是,“Make AI Write Like You”(让 AI像你一样写作)。或许未来,投靠硅基势力,让 AI代笔将成为一件更加顺利成章的事。
更快不代表更好,但总有利可图
自从 ChatGPT发布,总有乐观的声音说,由 AI完成重复的、乏味的工作,人类就可以做那些更有成就感、更闪耀人性光辉的事情了。
但对于一些人来说,现实恰好是反过来的。AI没有让人直接失业,但改变了他们工作的性质——更单调、更重复、更没价值感。
这些职位的存在,也说明了一个事实:目前的 AI还不一定能提供更好的内容,只是以更少的成本提供更多的内容。
AI比人类便宜,又达不到人类的水平,于是公司们以比过去更低的价格雇佣人类,让人类屎上雕花,荣光归于 AI。
但雕花改变不了原来就是一坨屎的事实。Miller在前司协助 AI产出的内容,直到他离职也并没有多少人看。
我制造了很多垃圾,这些垃圾充斥着互联网,也摧毁了互联网。
悄悄的他走了,正如他悄悄的来,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人属于社会动物,没有比“不被看见”更具挫败感的了。
给 AI加点“人味”,粉饰一下错误,其实已经算有些良心。放下身段,批量快速产出,哪管洪水滔天,才能在 AI时代攫取更多流量。
一个叫作 BNN Breaking的新闻网站,从2年前开始,通过 AI在短时间内发布了大量虚假信息。
之前它装得很“正规”,自称在全球都拥有资深记者,每月超过1000万访客。但仔细观察会发现,BNN的“记者”每分钟发表多次长篇报道,网站的图片是 AI生成的,文章的字里行间是明显的 AI味。

其实,BNN员工们主要是生活在巴基斯坦、埃及和尼日利亚的自由职业者,平时远程工作,将其他媒体的文章上传给 AI改写,每天产出数百甚至数千个故事。
这样的产出模式当然伴随着大量的错误,BNN被大量投诉,罪名包括事实错误、侵犯版权、诽谤名誉、捏造专家引言等。
然而,就像当年的“内容农场”一样,BNN这样的网站可以通过生产大量低质量的内容诱骗点击,利用搜索算法赚到更多的广告收入。他们的内容甚至一度被微软的门户网站 MSN收录。
巧了,因为 MSN也在用 AI取代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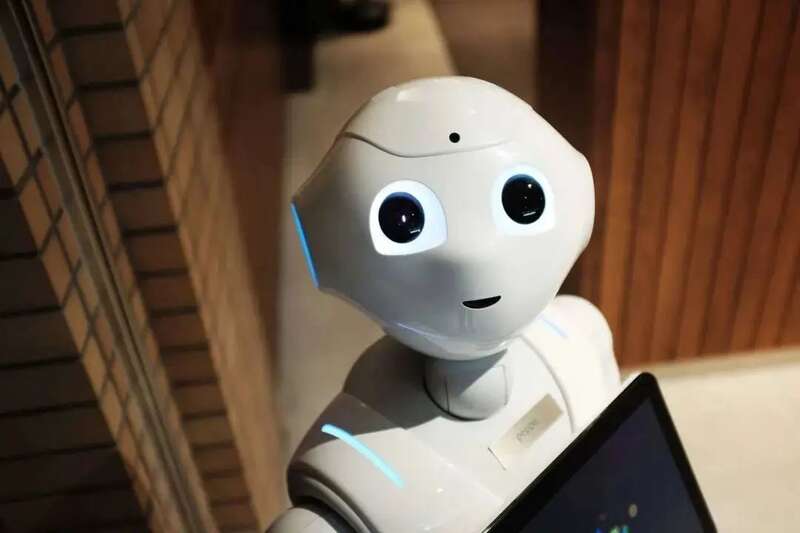
今年4月,BNN已经停止发布报道并删除了内容,网站也关闭了。但下一个 BNN还会不会出现,还未可知。
更快不代表更好,但更快确实存在短期变现的价值。不需要人或者把人的价值压榨到最低的产品,像水蛭一样吸血,分享到不该属于他们的蛋糕。
我们不是拒绝 AI,而是拒绝 AI生成的低劣内容。AI只是工具,而 AI味代表的,是一种不尊重人类、也不擅用 AI的逐利思维。
创造力总有出路
越是频繁使用 AI的领域,其中的人类可能越容易因为 AI感受到危机感。
今年2月的一项调查里,研究人员分析了2022年11月1日到2024年2月14日自由职业平台 Upwork的岗位变化趋势,判断哪些工作因为 ChatGPT受到了负面影响。
结果发现,岗位数量下降幅度最大的3个类别是写作(33%)、翻译(19%)和客服(16%)。
这便是事实,确实存在一些简单的文案工作,可以交给 AI代劳。但在趋势之下,也有积极挣脱困境的个人。
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
有些文字从业者站到行业头部,有自己的议价权,同时也在学习怎么更好地用 AI。
也有些文字从业者黯然离开,帮别人遛狗,学习怎么修空调。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体力活暂时比办公室案头工作更安全。

一则非常有名的反 AI广告
可能最被动的,恰恰是那些帮助 AI快速产出的“临时工”,他们几乎没有选择权,拿更低的工资,享受最小的成就感和安全感,等待被辞退的一天,也封死了创造力的出路。
第三国家的数据标注员们是这样,去 AI味的写手们也是这样,《大西洋月刊》将这些人称为“AI下层阶级”。
我们无法站在道德制高点,何不食肉糜地指责他们的选择。对于他们来说,为 AI打工,只是当下养家糊口的一种方式。
但对于我们自己,或许不应该陷入等待被淘汰的境地。
真正使用 AI的人会发现,我们平时用 AI不像测评那样,让它做个题、生成个图片、写个小游戏程序,大部分工作是无法交给 AI全权处理的。
比如在我的使用过程中,更多是用 AI了解某个陌生领域、陌生知识点,快速入个门,真的要写些什么,还得是自己来。
搜索引擎骗点击的文字、站在版权灰色地带的歌曲、开屏的 AI生成广告,至少在目前,AI在大多数领域,玩的还是冲量的游戏。
生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过剩了,互联网已经变得太无趣了,但好的作品仍在等待它的作者,以及它的观众。
以前我们泛泛地说,不是被 AI替代,而是被善用 AI的人替代。
现在,这句话有了更具体的含义,不要恐惧和抵制 AI,不要成为被选择的人,不要成为随波逐流的人,不要成为被 AI决定命运的人,而是保持好奇、兴奋和谨慎乐观,在我们自己所在的领域,坚持创作,努力创作得更好,时间会给出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