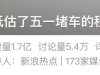因为中国学生喜欢待在一起,加上语言障碍,他们真正接触美国生活的渠道,可谓少之又少。虽然人在美国,却仍是在通过教材,了解着美国文化。
“他们在强化班上课,就像生活在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世界的夹缝间。”黛西试着总结说。
泡泡还好,她的口语不错,通过语言考试后已正式开始学习专业。尽管身边有了很多美国同学,但她依然觉得交流困难,“有些美式笑话,我根本听不懂,就只能跟着笑。”
俄亥俄大学的校园很漂亮,是标准的美国大学校园。中国学生初来乍到时,都挺兴奋的。但是,当他们在英语强化班待上一年半载后,普遍有种挫败感。
“我想在真正的大学课堂里学习,过上更地道的美式校园生活。但我只是看着美国学生走过、路过,在食堂一起吃饭,我无法体验到那种生活。”克莱拉说。
“天天学着一模一样的东西,看不到希望和尽头。”一个在英语强化班待了一年半、5次托福考试均告失败的男生说。
黛西感觉,他们好像被这门课给卡住了。
他们聚在一起,抽中国烟,说汉语,聊英语课、聊作业、聊家乡
在采访英语强化班负责人时,黛西第一次听说了“中国城”。

俄亥俄大学的“中国城”
“他告诉我,中国学生最集中的一个地方,是‘中国城’,他们同住在那一幢楼里。当时我吓了一跳,完全不能相信,因为我觉得这事太奇怪了。你知道,当我到国外读书的时候,我可不想跟一帮美国人住在一起。这样做,对很多事情都没好处。比如,你就没办法接触语言,我的报道里有一句引语,就是说‘这不是学习语言最理想的状态’。”
她决定一个人,去“中国城”亲眼看一看。
“中国城”的正式名称叫做斯科特楼,它实际上是俄大的一栋留学生宿舍楼,因为住的中国学生太多,被人称为“中国城”。虽然现在中国学生已被分散到了其他宿舍楼,但去年的时候,这里共住了215名学生,其中180个是中国人。
“中国城”的入口是一座红砖砌成的拱廊,上头挂着灯笼。顺着这些灯笼走下去,就到了一座露天的院子。院子里有片草坪,还种着樱桃树,中央由4只木制长凳围成了一个圈。
环绕着院子的这栋宿舍楼,十分雅致,一共有4层。一层是教室,上面3层是学生宿舍。夜晚,一排排白色的窗框里,射出温暖的金色灯光,整栋建筑,像一个镂空的立方体。走廊里,可以看到一扇扇门上,用汉字做的装饰。
黛西一个人在楼道里晃,碰上了宿舍管理员。在交谈中,她得知,当天晚上,这里要举办专为中国留学生准备的迪斯尼主题派对。
为了丰富中国学生的社交生活,不让他们长时间待在宿舍里,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精心组织了很多活动,有迪士尼卡通主题电影晚会,也有在当地年轻人里很流行的化妆舞会。
在一次化妆舞会开始前,宿舍管理员打扮成白雪公主的样子,挨个敲宿舍门,邀请中国学生参加派对舞会。
舞会上,黑白金三色的气球,被用胶带粘在墙上,以遮住原本严肃单调的建筑风格。“女士们穿着修长的露肩礼服,缀满水钻的细高跟鞋,在脏兮兮的灰色地毯上蹒跚挪步。男士们则穿着不合体的西装,从裤腿可以看出明显大一号。安迪戴了个灰色领结,正和泡泡吵架。克莱拉没来,宅在屋子里。”黛西回忆她当时看到的场景。
舞会办得似乎并不很成功。“红黄相间的灯光,映照着面具下害羞的脸。多数中国学生,只是待在圆形舞厅边上的阴影里,三五成群,打趣闲聊,只是随着音乐的律动,微微弯一下膝盖。各种甜腻的亚洲风格流行曲,循环播放了一夜。”
黛西的许多照片,都是在“中国城”里拍摄的。她还在英文报道里,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在“中国城”看到的一个个场景。
每到日暮时分,“中国城”楼顶上就会点亮射灯,刹那间,这个散落着烟头的院子,沐浴在蓝色的光线之中。
一些人站在院子中央的小广场上,聚在一起抽烟。他们说的都是汉语,在聊英语课、聊作业、聊家乡。黛西凑过去跟他们说汉语。“他们对我很感兴趣,觉得我很有意思,觉得一个试图说汉语的美国人很好玩。”
比尔和6个朋友一起坐在长凳上,抽着中国烟,讲着各种荤素段子。他们都抱怨在这儿生活的无聊。比尔已经来了5个月,几乎没有美国朋友,只和中国人交往。课余,他要么在聚会厅里玩游戏,要么在体育中心打篮球。他的英语口语很差,看到自己上强化班的漫漫长路,心情黯淡。当时,他在考虑夏天回中国,突击准备托福考试。
克莱拉合上笔记本电脑,走出她的宿舍。室内,那张属于美国室友的床,依旧空着。她沿着走廊,走过一扇扇紧闭的门,到了聚会厅。她和两个新来的同学用中文聊天,看过了迪士尼动画片《大力士》,在迪士尼主题的涂色本上,用蜡笔画了一会儿画后,克莱拉便又回到空荡荡的房间。
另一间屋里,一群中国学生正在用电饭锅煮面条。面条里只放了葱和酱油,然后他们用筷子吃。因为宿舍内禁止做饭,所以他们用塑料袋罩住烟雾探测器,以防触发警报被抓。
黛西在报道中评价道:“这里几乎处处弥散着彻头彻尾、坚不可摧的中国‘特色’。”
这种“特色”可不止是食物。凌晨两点,在“中国城”3层的学生休息室,4个18岁的学生正在打麻将。摸牌出牌之间,这些年轻的中国女孩互相逗趣、闲谈。
“我胡了!”一个叼着香烟的女孩喊道。随后,她推倒面前的14张牌,向大家展示。4人开始洗牌,“哗哗”声代表着新一轮牌局的开始。
“删除麻将照片,快点删除麻将照片!”
英文图文报道完成后,黛西将这些作品发到学校网站,刊登在一个叫做“我们的梦想是不同的”的摄影项目里。她特意给照片里拍到的中国学生发了信息,并告知了英文报道链接。可黛西没得到什么反馈和回应,“只有其中很少的人,见面被我问起的时候跟我说:嘿,照片不错,看着挺酷的!”
2012年春天,网易的编辑跟黛西联系,说想发她拍的图片。黛西给他们传了40幅。后来上网的照片,是由编辑选定的。黛西还在期待中国编辑通知她中文报道发布的时间,却一直没等来。报道在中国已经发表了,她还不知道。

网络配图
第一个告诉她这个消息的是打来电话的泡泡。那时候是晚上九十点钟,黛西在自己房间里,正准备泡一杯热茶。“她第一句话就问我:黛西,你是不是把你的照片,发给了一个中国的网站?我回答她,对啊!然后,她在电话里拉着长音,缓慢地说:好……吧……”
泡泡打电话的主要目的是警告。她告诉黛西,现有有些中国学生很不开心,他们想要找你,跟你聊一聊。黛西说,好啊,你可以把我的电话给他们,我很愿意跟任何一个想找我的人,聊一聊这件事。
放下电话后,黛西开始上网搜索这篇报道。紧接着,她接到了一个又一个的电话,一直到第二天凌晨4点钟。“那天晚上,我差不多接了50多个电话。有些是同一个人,翻来覆去地打给我。他们显得很烦躁,很气愤。虽然第二天我还要上课,人已经累趴下了,但我还是想跟他们解释清楚,我觉得需要有一个沟通的过程。”
有个男生给黛西打来电话,上来就问:你家在哪里?地址是在哪里?我现在要去你住的地方找你!黛西回答说:不,今天太晚了,如果你想见我,我明天可以去找你。
讲了半天,男生还是很气愤,他对黛西叫道:“你等着,我会去告你,让你坐牢!”
“我感觉,他们把这件事看得过于严重,夸张了,说了很多偏激的话。他们说这件事毁坏了俄亥俄大学的声誉,他们的文凭,现在一文不值了,以后会找不到工作。”黛西说。
整件事情中,最让她感到难受的部分是关于安迪。
安迪也打来了电话,他也很不高兴,因为他的爸妈看了照片后非常生气。黛西跟安迪见面时,他正好接到父母的电话。“电话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安迪找我,要我把报道撤下来。”
几乎每一个给黛西打电话的人,都要求她把照片撤下来,把整套新闻图片都撤下来,但是黛西拒绝了。“我跟每一个人解释原因,告诉他们,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我很想发表这个报道。”
直到现在,黛西依旧困惑: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跟她提及打麻将那幅照片?大家对这张照片,为什么那么反感?“每个人都在说,麻将照片,麻将照片,麻将照片。每个人都跟我吵:删除麻将照片,快点删除麻将照片!”
在照片里打麻将的女孩,也给黛西打来电话。第一天打了6次,第二天又打了4回。“她说我根本没有权利使用这张照片,这是她的照片。她叫我把照片从网上全部撤下来。我直接跟她说:没门!”
黛西发现,在图片版权观念上,他们之间是有差异的。“在这里,如果我给某人拍了照片,这张照片是属于我的,属于摄影师的。但是,在他们的概念里,似乎照片应该属于被拍的人。”
于是,很多人又把电话打给泡泡,因为知道她跟黛西的关系最好。“我觉得泡泡承担了很大的压力,大家都要她来说服我删除照片,最后我就同意了。”
事后,黛西却感到后悔。
“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我不应该删除这张照片。因为,此后每个人,都希望我把他们的照片删除,我不应该妥协才对。而且在一组照片中,删除一张也不会改变主题,但当时我妥协了。”
他们在渐渐改变,变得独立起来,想依靠自己而活、为自己而活
现在,让黛西郁闷的是,她从没料到,这件事成为这样的局面。本来她以为,报道在中国发表后,还会像上次英文报道发表一样,那些中国学生会对她说:不错不错,照片挺好看的。但事实上,大部分人表现得很沮丧。
最初几天,黛西接的电话最多,她的手机通讯录里,新加了好多中国留学生的号码。“后来,电话一天比一天少,他们似乎慢慢冷静下来了。”
那个麻将女孩打过多次电话后,渐渐也不打了。“我觉得已经跟她把事情讲清楚了,最后她对我说:谢谢你跟我交流。”
她在跟中国学生通话时,试图解释的是:我为什么觉得这件事情非常有意义,这件事可能带来的好处是什么。“但我当时的感觉是,当一个人很生气的时候,他就是想要发泄,想把一些话说出来。所以,很多时候,我只能静静地听他们说。”
让中国学生不满的是,他们觉得编辑选用的照片,多是“负面”的。可在黛西看来,像看视频电影,跟朋友聚在一起做饭,一块玩玩游戏之类的事情,算不上是负面的。“如果我上了视频网站,我的父母就不会不高兴啊。”她还说,虽然自己很投入地学习中国文化,还在中国生活过,但中国人的好多想法,仍让她琢磨不透,难以理解。
“可能是文化差异吧。”她这么归结道。

网络配图
在她眼里,这些中国学生,已经算是很爱学习的了。“俄亥俄大学的学生,爱玩是出了名的,以开狂野派对著称。学生的交际场所,主要是在酒吧。跟那些天天泡吧的美国学生比,这里的中国学生好很多。他们很少出门,很少喝酒,聚会时,无非打打小牌、玩玩游戏、煮煮面条而已。可他们的父母,还会那么生气。”
“他们打麻将,也不是没日没夜地玩,只是在周末才打,而且也不赌钱。”黛西像是在替这些中国学生辩白:他们才十八九岁,突然间,被抛到完全陌生的异国他乡,人很难适应,会令他们“文化休克”,会倍感孤独。他们想家,想念家里好吃的东西。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国内并不打麻将,但是现在他们需要这些“中国的东西”,他们聚在一起,玩中国游戏,上中国网站,做家乡饭吃,会令他们心里好受一些。
“一些中国学生,在这里每天就是学习,没有其他想法。但我们不同,我们有很多未来的计划。”黛西说,从小父母就鼓励她做一个独立的人,自己做事,自己承担。
18岁上大学时,她最大的期待是自己的大学生活能与众不同,希望自己尽快长大,更加独立。19岁时,她独自坐上长途大巴,游遍美国南部。大三时,她去了智利的圣地亚哥,学拉美政治和西班牙语。后来去中国,行前她一个中国人都不认识。
刚上大学时,黛西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将来要做什么。她先是读社会学,又选修了哲学、英语、政治等许多门课“做实验”,看看自己到底对什么有兴趣。直到上了大三,才发现自己热爱新闻,喜欢与人聊天,想知道别人的故事。于是,她决定从事新闻摄影。
在昆明,黛西住在郊外一个小区里,周围都是中国人。她每天骑着自行车四处溜达,给街上遇到的人拍照。去大理和中甸旅行时,她感觉自己像是被时光穿梭机送到了另一个时代。在广州,她待了6个月,在黑人社区生活、拍片。她有两部作品,在今年的美国大学生摄影年赛中获奖。
“4年大学,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找到了自己的热情所在。”她说。
对那些正在俄大上本科的中国同学,黛西更多的是寄予同情。
“到了美国,他们或多或少都会改变。一方面,他们受到中国那里、家庭那里来的压力和期待,被迫接受家长所做的种种安排;另一方面,他们人到了这里,处在美国大学自由开放的环境下,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他们在渐渐改变,有了想做自己的愿望,变得独立起来,想依靠自己而活、为自己而活。”
黛西表示,不满意网易编辑为她的报道所起的标题:“失落的留学梦”。
“那不是我要表达的主题。我的英文报道的题目叫做‘not here or there’(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我想表达的,是一种被困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感觉。”
“我为他们拍照片时,关系曾是那么亲近。但是现在,我觉得要给他们一些时间,让这场风暴慢慢过去。”黛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