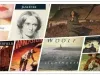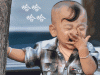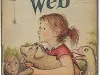陈企霞没有想到,因为一篇小说,他会被拘禁277天。
他是一个性格高傲的人,看人总是昂着头,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还说话带刺。周围人对他多少有些畏惧,避之唯恐不及。即使在遭到批判时,他也敢同周扬硬顶,绝不低头。直到一个爱他的女人,站出来揭发他不为人知的秘事,他才突然崩溃,从此低下了高昂的头颅。
1953年11月20日,《河南日报》发表了李准的小说《不能走那条路》。这篇小说描写了几个不同的农民形象,表现了农村中社会主义思想对农民自发倾向进行斗争的胜利。
文章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1954年1月,《长江文艺》转载了这篇作品。中南局文联负责人于黑丁对此发表文章给予高度评价。
《文艺报》分工阅读中南刊物的编辑侯敏泽,在编辑部汇报会上谈了自己对小说和于黑丁文章的看法,认为小说有明显缺点,而于黑丁文章对小说有过火捧场,是“拔苗助长”。副主编陈企霞同意侯敏泽的看法,要侯敏泽拟出写作提纲,形成文章后,在编辑部内部进行了传阅,再经他亲自修改,以“李琮”的名义发表了出来。
几乎是紧随其后,《人民日报》在1月26日全文转载了李准的小说,并在编者按中说:小说的人物描写真实、生动,是近年来表现农村生活的比较好的短篇小说之一。
谁也没有想到,如此一来,事情竟会走到阴差阳错的地步。党报《人民日报》肯定推崇的小说,竟然受到了《文艺报》的粗暴否定。
更令陈企霞想不到的是,《人民日报》是有来头的。最高层看到了李准的小说,比较欣赏,指示在《人民日报》转载。这一点陈企霞始终是不知道的,但负责领导文艺的周扬知道。
为此,周扬召集作协党组会议,讨论《文艺报》刊登李琮文章的问题,认为是在跟《人民日报》唱对台戏。
在周扬发言时,陈企霞不时插话,打断并顶撞他。比如,周扬说:地方文联的主席(指于黑丁)《文艺报》不能随便批评,这是纪律性问题。陈企霞当即反驳说:过去并无此种规定。顶得周扬无话可说,只好答复说:过去既无规定,那么以后注意就是。此前,《文艺报》发表评论,是比较无所顾忌的,对于像文协主席茅盾主编的《人民文学》,也会毫不客气地点名批评,又何况地方文联的主席呢。
但接下来的顶撞,陈企霞就犯了大忌了。周扬说:《人民日报》转载李准小说并加按语,《文艺报》却说这篇小说有缺点,岂不是故意同党报捣蛋,唱对台戏?陈企霞闻听,当即插话,提醒周扬注意,《文艺报》李琮文章的发稿时间,要早于《人民日报》的转载。陈企霞问道:“这恐怕并不能说是有意反对党报吧?”如此反问终于让周扬大为愤怒,当即拍了桌子,不准陈企霞发言。并质问《文艺报》在通报中发表读者来信,“专挑拥护李琮文章的”,这不是“利用群众意见来威胁党”又是什么?
这样的指责已经上纲上线到很有点尖锐了。
会议后,周扬决定写篇文章来反击《文艺报》,指定由康濯撰稿,即《评〈不能走那条路〉及其批评》。文章写出后,经过周扬、林默涵等人修改,发表在1954年第7期的《文艺报》上。
这篇文章在《文艺报》发表时,主编冯雪峰专门写了按语,承认《文艺报》对小说的看法不对。
陈企霞对此并不认同,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表示“这文章打击文艺报过火,保护于黑丁的文章不必要。”陈企霞的固执己见,为自己换来的只是一场无情打击。
1954年12月8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通过了改组《文艺报》的决议,其中第一条就是:撤消陈企霞同志所担任的《文艺报》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职务。
其实,还在开始讨论李琮的文章时,陈企霞就已经被剥夺了工作,实际上处于一种“失业状态”。对于性格刚强的陈企霞来说,被这样对待,是很难令他接受的。还在刚刚进城那会儿,因为一点小事,他与周扬发生冲突,周扬斥责他说:“你这算什么共产党员!”他当即回击:“你这算什么领导!”以周扬在文艺界的地位,没人敢这样对他讲话,唯独陈企霞敢。然而这种脾气,早晚是要付出代价的。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陈企霞仍然拒不认错。为了替自己辩白,他采取了一个很不明智的做法,给上面写了一封匿名信。
1955年春,作协收到公安部转来的一封信。公安部方面初步判定,写信人来自作协内部。刘白羽把信交给副秘书长张僖处理,张僖就带领手下工作人员开始查对笔迹。但找了很长时间,发现与作协任何一位工作人员的笔迹都不相符。尽管如此,作协和公安部仍然判定,匿名信就出自作协内部人员之手,而且写信人就是陈企霞。
这封信确实是陈企霞写的,但他一直不承认。
到了7月底,当作协认定匿名信是陈企霞所为时,立刻将他从安徽梅山召回进行调查。在8月初的一次对陈企霞的批判会后,冯雪峰揭发说:陈企霞曾经说过,他有一支手枪和两颗子弹,一颗子弹要打死他最恨的人,另一颗要留给他自己……
因为此前已经发生过田间私藏枪支的“自杀未遂事件”,现在冯雪峰揭发陈企霞也有枪支,大家顿时感觉事态严重,于是指派张僖和刘白羽、严文井三个人到公安部作了汇报,当时六局的局长陈中又向公安部长罗瑞卿作了汇报。罗瑞卿作了批复,于是公安部就派人到陈企霞家,是由康濯和张僖陪同一起去的。
接下来就发生了陈企霞突遭拘禁,家中被搜查的事情。
这一天是1955年8月19日,星期五。虽然是工作日,但那天陈企霞全家却都在家。孩子们正放暑假,妻子郑重因为小女儿陈幼京尚未满月,在休产假。至于陈企霞本人,连日来一直不停地开会,这天刚好是个空隙,他给自己的安排是洗一个澡。
下午,他正在卫生间洗澡,此时家中进来一个人。来人叫康濯,原来是丁玲领导的文讲所的副秘书长,不久前刚进入作协肃反领导小组。这个小组一共五名成员,分别是刘白羽(作协党组副书记)、严文井(作协秘书长)、张僖(作协副秘书长)、阮章竞(作协机关党总支书记),以及康濯,组长刘白羽。
康濯和陈企霞是老同事,过去经常上门谈工作或是聊天。但今天的康濯却表情严肃,陈家孩子当时正在听收音机,一见他那副模样,赶紧关了收音机,躲到隔壁房间去了。郑重上前招呼,也看出对方态度冷淡,于是提高声音,告诉正在洗澡的陈企霞:康濯来了!不明就里的陈企霞,还如往常一样随口答道:“你请他稍等一下,我马上就好。”
过了一会儿,陈企霞从卫生间出来,脚踩拖鞋,身上穿着睡衣睡裤。“我去换下衣服。”他对康濯说。尽管很熟,这样相见也并不合适。但康濯拦住他,说不用了,请他到门外说几句话,陈企霞也没多想,就穿着拖鞋和睡衣,随同康濯走了出去,并随手把门关上。
很快,门外就传来了陈企霞激动的喊声:“你们这样做是完全错误的,我要向上级控告你们……”但随即声音就由大变小、由强变弱,直至消失。又过了一会儿,响起了敲门声。郑重开门一看,是康濯一个人站在门外。他进门后,把郑重拉到一边,嘀咕了几句,几个孩子看见母亲的脸刷地一下变白了。
郑重去给丈夫取衣服,康濯则开始搜查陈企霞的抽屉。康濯走后,郑重对几个孩子说:你们的父亲被隔离审查了,是组织上的决定,我是共产党员,只能服从。
康濯返回来是搜查手枪和子弹,但一无所获。他走后,作协的人事科长又上门来找了一次,还是没有找到。最后是郑重在家中另一个地方找了出来,共计手枪一把、子弹六发、持枪证一份。她把这些东西包好后,吩咐大儿子送到楼下的作协人事室。
陈企霞被带走后,家里人并不知道他去了何处。直到第二天早上,看守人员来陈家通知给陈企霞准备早饭,一家人才知道陈企霞就关押在作协大院里。当时的作协,既是机关,也有宿舍,陈企霞一家就住在大院里。饭做好后,大儿子陈恭怀给父亲送饭,才发现平常到处乱钻的大院里,竟然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
陈企霞从此失去了自由,在拘禁状态下度过了277天。直到1956年5月22日,中国作协宣布解除隔离审查,陈企霞才恢复了自由。
拘禁期间,副秘书长张僖曾对陈企霞妻子说:“被捕前是为了匿名信问题,逮捕后变成了丁陈反党集团问题。”原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拘禁陈企霞的真正目的,是要震撼、动摇、击溃丁玲。陈企霞被关后,外面对丁玲的斗争随即进入高潮。文讲所方面,原本是丁玲下属的康濯,积极参与了对丁玲的斗争;假如陈企霞在长期的拘禁之中耐受不住,也反戈一击,揭发丁玲,那就是这场斗争的很大胜利。
但陈企霞拒不合作。他不但把强加于他的指控否定得一干二净,也拒绝揭露丁玲。他甚至转而指控作协领导对他搞“逼供信”。因为查不出匿名信的任何线索,陈企霞又矢口否认,外调也找不到他的历史问题,再关就毫无道理,于是作协只好不了了之,将他放回家中。
如果不是57年反右发生逆转,丁陈反党集团的事情很可能得到平反。结果上天不佑丁陈,反右来临,丁陈事件不但没有得到平反,二人还被划成右派。
而且飓风猛刮之下,突然出现了两个意外情节。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个姓周的女编辑,揭发陈企霞的匿名信,是通过她找一个老秀才誊抄的,然后陈企霞去了上海,是她把信寄出去的。
作协当即派人去了女编辑家,女编辑领着大家找到了替陈企霞抄信的老秀才,最后证明女编辑说的是事实。
这个被陈企霞顽强守护了两年的秘密,就这样破获了。
匿名信刚有下落,天津方面又传来消息,女作家柳溪同意开口揭发陈企霞。
这两位女士,与陈企霞都有特殊关系。柳溪还是当时有名的女作家,她在《人民文学》发表的小说《爬在旗杆上的人》,在读者中引起过热烈反响。
柳溪之所以卷入陈企霞案中,是因为她替陈企霞打抱不平而受到牵连。陈企霞被拘禁时,她也被隔离在一间小屋中,每天写交代材料。门外有流动哨监视看管,有时还被押到批斗大会现场参与陪斗。在陈企霞解除隔离后,柳溪也随之获得自由。然而反右斗争一来,柳溪再次承受了巨大压力。
作协方面曾派刘白羽专程去了一趟天津,动员柳溪开口,柳溪拒绝谈她与陈企霞的关系。但仅仅过了一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柳溪却突然改口,表示愿意吐露实情。
作协方面于是作出安排,一定要利用好这个突破口。在7月30日的斗争会上,从天津赶来的作协主席方纪做主要发言,初步透露了柳溪已做交代,但全部情况还没有和盘托出,目的是诱使陈企霞自己坦白。7月31日的斗争会仍然如此。8月1日下午,决战打响,据郭小川日记记载:“曹禺第一个发言,很精彩。然后是柳溪长达两小时的发言,血泪控诉。”
这天晚上,陈企霞同妻子有一次彻夜长谈。第二天一大早,陈妻来到刘白羽家,“把昨晚听陈企霞说的事一五一十告诉了刘,说陈企霞现在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刘白羽据此安排郭小川在办公室接受陈企霞的交代。“十时,陈来,情绪紧张,首先就交出钥匙两把,而且说:这是罪证!然后又滔滔不绝地交代了他与丁玲、冯雪峰的关系。”从上午十时一直讲到下午一时。郭小川说:“不断使我毛骨悚然。”那两把钥匙,是陈企霞与两位女性幽会地点的钥匙。
一直绝不低头的陈企霞,因为两个女人的揭发,终于意志崩溃。
8月3日,大会检讨一开始,陈企霞便坦白说:这几天,我可以说已经死过一次。这两天我是发抖的,但还是坚决抗拒。柳溪讲话时我对她充满了仇恨。前三次会议我只想一个问题,即如何死。那时我觉得天昏地黑,看不见太阳光。上次会议后,我下了死的决心。买了两瓶白酒,找出两个金戒指,想吞金而死,但又怕遇救,准备同时吃火柴。并准备写一封非常恶毒的遗书。柳×发言之后,遗书改了。
这个“改”字,透露了一种动摇,郭小川的日记分析说,柳溪的“血泪控诉”会起到一种效果,使人们几乎不会同情他,这样的话,他以死来报复某些人的愿望就很难实现。
为什么没完没了的斗争会,充耳盈目、声色俱厉的指斥、怒喝,乃至身陷囹圄277天这样的煎熬,都没有摧毁陈企霞,而两个女人的揭发,却让他一溃千里。只能说,他最隐秘的“私房话”、他一心一意想深深埋藏的东西,被公之于天下,将他做人的尊严彻底毁灭。这让曾经是那样高傲的人,情何以堪?留给他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结束生命,要么苟且偷生。而活下去的代价,却是抛弃尊严,接受屈辱。他最终选择了后者。
陈企霞逝世后,大儿子陈恭怀有次去看望严文井,后者回忆说:“那时候(指五十年代),企霞看人总是抬着头,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说话带刺。我们对他多少总有些畏惧三分,唯恐避之不及。”
这个“总是抬着头”的陈企霞,最终被收拾得服服帖帖,从此低下了自己高傲的头颅。
资料来源:
李洁非《屈服——陈企霞事件始末》(原载《钟山》2009年第3期)
王增如李向东《“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冤案形成始末》
2022-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