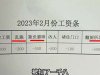东莞,中国外向型出口企业的大本营、“世界加工厂”,一定程度上,“中国制造”也是“东莞制造”的别称。因其地近香港,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承接了大批由港台转移而来的制造加工产业而迅速崛起,成为自由经济全球化布局的一个中国缩影。
短短30年,东莞已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农业小县,一跃成为南粤重镇,2007年,以一个常住人口只有650万人的地市级规模,其GDP却高达3000多亿,几乎可称得上“富可敌省”。
温家宝总理曾在多个公开场合说,他最担心的是广东。去年9月起,“空心化”、“东莞减速”开始频频见于报端。至去年底的短短数月内,温总理先后4次造访广东。东莞,正是他调研中国经济的一支水银针。
东莞怎样了?东莞在发生什么?特别是东莞曾经接收的千万名外来工,在短暂返乡后,有没回来?回来后能否找到工作?那些在城市边缘长大、不愿意回乡的外来工第二代,该怎么办?
在某种意义上,观察东莞,观察农民工能否就业,不仅是我们探测中国经济是否已到底部、即将步出低迷期的一个标杆,也是中国能否实现顺利转型、真正建构“和谐社会”的沉重却又极其必要的一步。
我们还是从一群东莞人物入手,他们是:本地东莞人、工厂主、成年外来工、年轻的外来工第二代。他们的生活转折,也许正是千万东莞人的缩影。
陈景池 到处救火的本地村长
“现在我每天晚上都要吃止疼粉”
本刊记者 王大骐 实习记者 李少卿 发自东莞
正午,汽车行驶在东莞宽敞的马路上,两边的店铺大都拉下了铁闸,偶尔开门的几家饮食店门口,稀稀拉拉地坐着几个食客,周边的工厂铁门紧锁,只有一两个保安坐在门口无聊地玩着手机。
车子拐进一条小街,开进了一家皮具加工厂的大门,我们随厂长上了楼。
“原来工人多得坐到墙边上,加班订单都做不完,要外包出去给小作坊做。可现在你看,全停下来了,原来800人的工厂,我们已经减到了100多人。” 站在往日喧闹但现在空荡荡的厂房里,旧锡边村村长、也是该厂厂长的陈景池很有些失落。
游师傅说自己能体谅工厂的难处,不过他还是准备走,“如果东莞这边实在找不到工作,就回广安去,广安的发展也不错,等以后经济变好了可以再出来嘛。” 游师傅说自己虽有信心,但看着空空荡荡的工厂,还是会有“英雄迟暮”的感觉。
我们问经理能否采访厂长,他说,厂长最近一直在外面陪两个大客户,争取订单,很少回来。
我们要工作 --3个中年外来工的故事
半年前,郭小明3人还是东莞一家台资大厂的同事。随着工厂倒闭,他们的命运也随即发生变化
本刊记者 刘子超 发自东莞
"好像一夜之间什么都没了"
郭小明扶着自行车站在东莞天华家具厂门口,腋下有一圈汗渍。这里是虎门,烈日下,绿色的厂房显得空旷、孤独。许多次,他在薄暮中经过这里,都会发现门口的美人蕉已经枯萎,蛛网在角落里结成了肮脏的绒花。
"我在这里工作了11年,"他对看门的老人说,然后安静地抽上一支烟,像在费劲地等待天明。
如今,37岁的郭小明在兴义玻璃厂做检验员,薪水还不到从前的一半。1997年,他进入天华家具厂。工厂倒闭之前他是包装部的组长,每月能拿到3000多块钱。
郭小明记得,去年10月份,当周围的鞋厂、电子厂纷纷倒闭时,做美国生意的天华工人还一度感到庆幸。尽管这家发展近20年的台资大厂也已经捉襟见肘,但没人相信它会突然倾圮。
一个毫无征兆的星期天下午,老板"跑路"的消息在600多名工人间不胫而走。当郭小明赶到厂里,他看到愤怒的供应商正要抬走机器抵债。"这事来得太突然,我们都不相信它是真的,"郭小明说。
最终,虎门镇路东村委会接管了天华厂,并且垫付了工人的工资。那天下午,厂子的操场上摆了长长一排桌子,工人按部门排队领最后一笔工资。大广播不停地播放着通告,告诉那些按完手印的工人,不要在厂区逗留。
年轻工人拿到钱就走了,可郭小明心里不是滋味。在工厂外的小饭馆,十几个工作十多年的老职工坐在一起低头不语,仿佛惶惑的未成年人,看不清未来的路。
"毕竟在这里工作了这么多年,"郭小明说,"好像一夜之间什么都没了。"
与郭小明一样,周荣钦也是90年代就进入天华厂。他曾想留在东莞,但找得到的工作都只几百块钱一个月,无法支撑一家花销。他最担心的还是上初三的儿子。
郭小明最终拿着本钱退了出来。春节过后,走在飘着雪花的湖南老家,他还是决定回到东莞。"我想找一份正当工作,只要它能维持生活,"郭小明说,"11年了,这里是我最熟悉的地方。"
漂泊,漂泊
对那些常年在外打工而如今失业的工人来说,家乡已经显得不够亲切。当城镇化的车轮碾过他们的故土,很多人变成了没有土地的农民--这也是肖平良决心漂泊在外的原因之一。
十多年来他一直生活在天华厂,每个月只休息一天,平时甚至很少离开虎门镇的路东社区。肖平良已十分习惯这里的世界,但一夜之间,他发现这个生活了十多年的城市没了他的位置。遥远的金融风暴呼啸而来,他们被骤然甩出运转了十多年的轨道。四处找工的生活并不轻松,仿佛鞋肚里有一颗石子,每走一步都是痛楚。
"我不敢进小厂,怕过几天又会倒闭,"肖平良说。"小厂没有保障,说倒就倒了,没有人管你。"
而在这场金融风暴中,"世界工厂"受挫甚深,许多大厂一夜猝死,硕果仅存的企业也在尽量压缩人员,削减成本,努力维持。根据3月3日广东省劳动保障部门的统计,节后入粤的农民工有946万人,其中的46万人未实现就业。
"东莞的人才市场我们也去过,"肖平良说,"但那里都是进公司的,像白领一样的工作。"
"其实我还是想进家具厂。做了10年家具,只有这方面能得心应手。"可是家具行业在东莞正值举步维艰。在被称为"东方家具之都"的东莞厚街镇,当地劳动部门的调查显示,家具行业的开工率不到60%。理想的工作找不到了,他们都务实地降低了自己的标准。在东莞找工无望,肖平良去了广州花都,投奔弟弟。
郭小明还留在虎门。他看到了兴义玻璃厂的招工启事。要招15人,赶过去一看,来应聘的就有100多人,满满地站了一操场。先是查证件,之后考文化知识(其中一题是要写出四大名著的作者),面试后还要做俯卧撑--玻璃厂干的是体力活。
俯卧撑做到26个,他喘着粗气趴在在地。管事的人说:"看你年纪大,有家有口的不容易,多算4个算是见面礼吧。"
郭小明说,他一直想去谢谢这个人,可感激更像是种苦涩。比起那些至今失业的同事,他觉得自己幸运得多。
"这是没办法的事,美国那么大的银行都倒了,大河里的水没了,小河也要干,"郭小明说,"一次看电视,看到美国人过圣诞节,很多东西原来可以买,现在也算了。看看外国人,再看看自己,觉得是安慰,又好像不是。"
如今,郭小明在尽力缩减开支。原来租240元/月的房子,现在搬到了180元/月的地方。原来买过一双安踏,现在再也不敢买了。他天一黑就到社区广场上,看老年人唱歌跳舞,打发时光。
无所事事的时候,他忍不住怀念已经不复存在的天华厂:"老板对我们不错。十多年了,工资一次都没拖过。平时大家相处得也融洽,工作压力也不大,有了这些,还图什么?我本来想在这里一直做下去的。"
十多年来,郭小明们固守同样的位置,忙碌同样的工作,聚沙成塔般营建起稳定不变的生活。如今,天华厂这个微型世界轰然倾圮,他们忽然发觉自己的身份十分尴尬,甚至不能再被称为"打工仔"了--他们已经与这个称谓里隐含的年轻无畏相距甚远。他们被生活推动着,抬腿出发,但自己也不知道哪里是下一个落脚点。
在花都的广州火车北站,四下都是喧闹的人声。肖平良畏缩地站在街角,等着弟弟来接他。他的脸色疲惫紧张,在阳光下泛着蜡一般的光色。直到看到骑着助力车的弟弟,他才如释重负地露出笑容。他挤出人群,小心翼翼地坐到弟弟的后座上。在汽车的喇叭声中,在城市的喧嚣声中,他们摇摇晃晃地,越骑越远。
不想回去的小夏
"在这每天见到的是人,是汽车,回老家每天面对的是猪,是牛车,你会回去吗?"
本刊记者 王大骐 实习记者 李少卿 发自东莞
东莞桑园工业区。
玩具厂的大门口立着一张红色的招工广告牌,告示旁,蹲着一群农民工,他们只是在交头接耳,可却没人敢进去。
小夏是其中的一员,正看着广告牌上的字:"包吃住,月薪800。"
"又是骗人的吧?"站在路边的小夏把记者当成了同行者。"我看起来年纪太小,怕他们不要。你们先进去,就说我们3个是一起的,这样成功率高。"
这个染着黄头发的少年,今年只有16岁,不过据他说从老家河南来东莞已有两年。原来在一家收音机厂做普工,"就是把零件凑在一起,往电路板上一粘,特别简单"。小夏说工作很无聊,但一个月有1000多块钱,工作时间也宽松,"计件算钱,每天只要能完成定量就行,多做还算加班费,1小时5元"。手脚灵活的他,经常很早就可以回去睡觉了。
今年1月,老板告诉小夏和他的同乡,要扣他们一个月工资,理由是"不服管理,打架闹事"。"其实就是老板没钱了,故意找碴。"小夏告诉记者,"以前我们打架,老板才不管呢。又没签合同,出了事你自己负责就行。这次,凭什么扣我们工资?"
小夏和几个同乡不服气,就罢工了一个星期。后来老板同意给他们发工资,但条件是拿钱走人。小夏和另外3个同乡一起离开了工厂。现在,同乡中有一个已回了河南,还有两个在东莞无所事事。
记者同小夏走进了玩具厂的值班室,刚好经理和业务主管都在。他们告诉记者和小夏:"现在宿舍不够住,暂时不招人,但可以填张表,以后招人直接找你们。"
走出玩具厂,小夏显得很平静,告诉记者他找了一个多月工,这样的表已经填了十多张。招工的大部分要技工,没技术的普通工人很少有地方要,有也只要女工。
这一情况在东莞非常普遍,金融危机下,各家工厂都在节省开支,女工吃得少,干活仔细,又比男工好管理,不会闹事。
此前他曾找了一家中介公司,说是"保证能找到工作"。在交了100多块钱中介费后,小夏被介绍到一家工厂做清洁工,进厂前又要他交了50块钱,说是进厂费。没干两天,工厂说要检查他的合同,合同刚交出去,就被人撕得粉碎,而后又以他"工作不努力"为由开除了他。至此,小夏说他"再也不相信中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