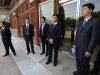十年砍柴
我们这些放牛伢子,除了一条仅仅遮住下体的裤衩外,都光脚、赤膊。太阳把瘦瘦的我晒成非洲黑孩子,脚板踩在发烫的青石板路上,时间长了都失去了感觉。黄昏,太阳落山许久,牛们还不愿意归栏,死乞白脸地赖在小溪里、泥塘里,沉到水中后好些时候,牛才冒出头,鼻孔忽忽地往外喷水。人和牲口都很烦躁,只有晚饭后,我脱光衣服,躺倒门前浅浅的沟渠里,才觉得有一丝凉快和安宁。西边天地庵水库坝上的大马力抽水机没日没夜地抽水,经过沟渠灌溉着一丘丘渴极了的禾苗。流动的水,是洁净的水,水渠中的我枕一块石头,头露在外面,水从脖子开始,顺着肚皮趟过,轻柔柔的,很是舒服,小鸡鸡处在十分自由放松的状态,在流水的抚摸下,悄悄地起了变化。仰看满天的星斗,它们眨着眼睛看着我,耳边只有流水的声音以及蛙鸣,四野安静得很。偶尔有一声奇怪的呼唤,疑心在唤我,想起爷爷给我讲过的许多鬼故事,鬼勾小孩的魂,唤他的名字,如果一答应,魂儿马上就没了。于是无论怎样也不答应,哪怕真的有熟人喊我的名字。
山村的安静有一天被山外传来的恐慌打破了,听说北方很远的地方闹地震,死了很多人。我们那里的人只经历旱灾、水灾、山洪等等,没有谁见识过地震。于是这地震越传越可怕,好像就在你面前有一个魔鬼张开血盆大口。有老人说这是地底下的龙不安分了,龙一动身子山就倒下了,地开裂巨大的缝,房屋、牲畜、大人小孩,一下子就被这条龙吃了。我总觉得水库四周山里的大岩洞中间,藏着这样的龙,它要是生气了,就会吃人。
地震的地方究竟在哪里?连爸爸妈妈和大队书记都没去过那里,只有我二伯的三儿子运哥知道确切的位置,他刚刚复员回家不久。他在石家庄当兵,我从来没听说的地方。复员时回到家,我和一群孩子去围观,他穿一身没有帽徽领章的草绿色军装,从一个黄帆布大包里,摸出冰糖,一人发两颗。回家后妈妈听说我和弟弟比别的孩子并没有得到优待,有些生气地说他当兵你爸爸给找了公社武装部长,不然哪去得成?也是两颗糖,真不知道好丑。后来有队上的人问他用的是什么枪,他憨实地说,部队几年,除了新兵连三个月摸过枪外,就一直在当炊事员,喂猪、做饭。去那么远的地方喂三年猪?有人说划不来,也有人说见见世面总是好事。不过对运哥来说最大的收获是,许多人家办喜事,找他去帮厨。
地震越来越说越玄乎,有人说天老爷要来收人了,也有人说干脆把猪宰了,好好地吃几餐肉,不然死了太不合算了。大队干部终于站出来了,开大会告诉社员们,地震并不可怕,而且地震的地方离我们很远。但不能麻痹大意,要学会预防。于是社员之间相互传授了许多地震的土知识:比如井水突然变浑了,畜牲晚上不安分等等,有些也是被填油加醋,弄得荒诞不经。
一天半夜,哨子尖利地吹,这是平时开工用的哨子,掌握在队长的手里。原来当队长的华阿叔,他家的母鸡半夜打鸣,他觉得是地震的前兆,把沉睡的村民全部唤醒。那夜爸爸在四里外的卫生院,哥哥在公社初中寄宿,听到哨声,姐姐自己爬起来了,我和弟弟被妈妈唤醒。我记得妈妈还沉稳地为兄弟俩穿上厚厚的衣服,后来她说听人讲地震后天会变得很冷,所以让我俩多穿衣服有备无患。
一家人从屋里出来,往东边的茅屋山走,听说地势高的地方安全一些,地震后龙口里喷出来的水淹不着。全村的人都往哪里聚集,大人喊小孩闹,乱成一团。我提着我家的煤油灯,走在前面。觉得后面真有个野兽来追我似的,跑得飞快,将妈妈、姐姐和弟弟抛在后面。当大家都坐在山腰的草坡上歇息时,我还不知疲倦地往山顶上冲,似乎只有山顶才安全。妈妈在后面大声地喊我的名字,喊了好久才让我止住脚步。
当然是一场虚惊,天麻麻亮的时候,大家都回家休息,所有的人都在埋怨队长的冒失,说白白地浪费了灯油,耽误了困眼闭(我家乡睡觉的说法),强烈要求队长歇工一天。
地震的恐慌刚过,又传来了一则所有人都不敢相信的消息:毛主席死了。
那是一个的黄昏,天气还很热,西边是红红的火烧云。我们这些小孩还穿着小褂子、短裤在村口玩耍。在公社中学读书的全叔叔回来了,穿一件红色的跨篮背心,挑一担水桶去村外的水井挑水,经过村口时,和村口臭椿树下纳凉的酉爷爷说了一句:“毛主席死了。”
“你莫乱讲,这样的话能随便讲的!你想吃牢饭了?”酉爷爷一阵惊慌,说道。
“不是乱讲,乡里广播里广播了,我们老师也讲了。”
“毛主席真的去了吗?他去了,谁来管我们?”酉爷爷提出疑问。
“全老满,你肯定是乱讲,毛主席怎么能死的?他老人家是万岁,是长生不老的。”一位老奶奶死活不相信。
我们听说这话,也不敢相信。回去问妈妈。妈妈说:大概是真的,这样的话没人敢乱讲,除非他不想要吃饭的家伙了。
大队的大广播里面终于证实了,毛主席逝世了,最红最红的太阳落山了。在山村孩子的心里,毛主席就是住在北京金銮殿的大救星,就是慈祥得像爷爷一样的毛爹爹,就是挂在堂屋正中间的那张像,下巴有一颗痣,村里的老人说,毛主席就是这颗痣生得好,是菩萨相。我们小孩最先认识的字就是生产队队部墙上用石灰写的几个大字:“毛主席万岁”,我们会唱的第一首歌就是:“东方红,太阳升”。我们村里一个地主婆,用上面有毛主席语录的报纸剪鞋样,被发现后,大队干部说她想把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踩在脚底下。她被抓住游行,斗了个半死。
接下来,公社和大队都开始办丧事。大队的灵棚扎在小学校的操坪里,有大人从山上折下来的马尾松,有白花、黑幔和花圈,追悼会上有几个贫农代表声泪俱下地讲述毛主席的恩情,有一个老太太哭着哭着就晕过去了。
再接下来大队开始部署基干民兵荷枪实弹站岗放哨,对地主、富农等四类分子严加看管。走亲戚基本停止了,如果因孩子降世确实需要外出的,必须凭大队部开具的路条。由于我爷爷所住的老屋走廊是交通要道,民兵在这里设卡盘问过路人。有一个挑担子的中年人被挡住,没有路条,不让他过,他讲自己的成分是贫农,是哪个公社哪个大队的社员,叫什么名字,去哪里干什么。没人敢相信,先扣留,派一个后生跑到他所说的大队核实无误后,才开具已盘查的证明放行。
生产队保管员的二儿子,一个字写得不错的叔叔,在每家堂屋门的上方,用白粉刷白,画一个长方形的黑框,框框里用墨写几个宋体字:“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前些年我回老家,许多家门口这些字还在,也算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了。
在那个要布票的年代,那一年黑纱的供应好像不受限制。根据家里的人口,除“四类分子”和没有上学的小孩外,其他人每人一个黑袖章,一朵白花。我和弟弟没有上学,所以不发给黑箍箍,心里很不高兴,觉得自己受到了歧视,缠着妈妈要黑纱。妈妈没办法,只好从家里拿出黑布,给我们两人做了两个黑袖章,我根本意识不到什么悲痛,只是觉得人家有我也得有,有了和上学孩子一样的待遇,便觉得虚荣心得到了满足,而且那些日子有闹热可看。
上学的哥哥和姐姐回来后说,毛主席逝世后,他们最不习惯的是,每节课上课前,老师都要他们站立、低头,默哀三分钟,天天如此,厌烦了。妈妈告诫他们,此话只能在家里讲。
又是一个深夜,已是深秋,天气比夏夜凉多了。我们又被队长吹哨子吵醒,告诉有重要事情。妈妈起来点亮煤油灯,我也睡不着,非得跟着她出门看热闹。
这次不是闹地震这样的恐慌消息,而是一道大喜讯。队长带领几个人在我家屋后面,挨着生产队烤烟房空地上,敲锣打鼓,说是刚跟着大部干部,连夜从公社接来了宝像,让社员同志们请到家里,马上贴到墙上。
每家都是两张宝像,回家后在油灯下。一张宝像我认识,胖胖的头像,梳着大奔头,嘴下面有一颗痣,这是刚刚逝世的毛主席;另一张宝像,同样天庭饱满,同样双目炯炯,只是理了一个平头。看起来和毛主席长得差不多。
妈妈告诉我:这个人是华主席。
我问华主席是谁?
妈妈说毛主席死了,华主席来接脚的。
我打破砂锅问到底,什么叫“接脚”?
妈妈有些恼怒地说:原来毛主席当家,现在他老人家不在了,就让华主席当家,接着毛主席来管我们。
原来如此,但我还是似懂非懂。从来没见过毛主席和华主席,他们怎么能管我呢?又不像我妈那样能每天早晨拿着搅拌猪食的木棍,站在床前催我起来去放牛。
宝像回家不过夜,妈妈把堂屋正面原来贴祖宗神位的地方,用扫帚扫干净,熬一小锅稻米糊糊,恭恭敬敬把两张宝像贴上去。从此每天经过堂屋,就看到两个人眼睛盯着我,似乎在问我,今天做没做坏事?
过了些日子,哥哥和姐姐放学回家,高兴地说,这几天又不用上课了,去学校演戏,游行。那些日子,每逢大事,学校就停课参加政治宣传活动。
听上初中的哥哥说,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
四人帮是四个人,三个男的一个女的,简称王张江姚。什么叫粉碎?哥哥说用铁锤敲一个土坷垃,一敲就碎。什么叫“一举”?哥哥说就是举起拳头。华主席一个人伸出拳头,就把四个人打得粉碎,好厉害哟?那段时间,华主席在我心目中的印象,不是什么领导人,而是武林高手。
有热闹看,我当然不会放过。在家我还埋怨那一年妈妈为什么不送我上学?本来秋季开学时我缠着她要去报名,后来小学里的老师说,五岁,太小了,再等一年。
哥哥已去公社的初中,姐姐还在小学校。小学校离我家两里地,姐姐哥哥们带弟弟妹妹上小学校,是当时很正常的场景。小学校刚修建后,哥哥在这里读了五年级,那时还没有课桌,一块木板用砖头架起来,每人从家里搬来小凳子,高高低低地坐在一起。
等到打倒四人帮时,学校已经有了统一制作的桌椅。我家山区多树木,大队又有好些木匠,就地取材没什么难的。老实说,直到我前些年做记者去西部某些省区采访时,看到一些乡村学校还不如我记忆中家乡的小学校。
学生们在操场上先是开会,然后呼口号,什么“打倒四人帮,人民喜洋洋”,“打倒害人精,人民得翻身”之类。开完会就游行,游行打着红旗,绕七个生产队的居民点转一圈,一路上小学生呼口号,背毛主席语录,什么“排除万难,不怕牺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再唱歌,“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部带了头,群众有劲头”之类。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高年级学生,举着标语和画像,那画像是学校老师画的王、张、江、姚的头像,有的是大板牙,有的是秃头,有的像老巫婆。
我记得很清楚一幕,游行队伍到了一个村庄,一个老头指着江青的漫画像说:真是怪事,长得这样丑的女人,毛主席也不嫌弃,娶了做婆娘。给我我都不要。
游行庆祝完了以后,学校开始排戏。每个班都在演打倒四人帮,那些不听话的调皮捣蛋鬼,被老师说成是四人帮一类的人物,演戏时站到讲台前面,面对全体同学,分别饰演王、张、江、姚,弓着背,下面的学生装革命群众,控诉完了,一起振臂高呼:打倒!
打倒四人帮的戏演完后,学校老师排演《园丁之歌》,说的是一个后进生不听话,贪玩,后来在老师的教导下发奋学习的故事。这个戏有情节,难度比较大,非小学生能信任的,学校的几位民办教师亲自涂抹油彩上场。大队书记的儿子,我叫斌叔叔的,刚代课半年,长着一张娃娃脸,他饰演那个不听话的刺头学生,拆了算盘珠子,做玩具火车的轮子,我的亲婶娘,嫁给我在县城工作的叔叔好几年了,也是民办教师,演一位苦口婆心的教师。
那两年,孩子们跳橡皮筋的歌谣都改了,改成:“回到家,推开门,一举打倒王洪文;……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一举打倒姚文元。”我当时疑惑非常,为什么捡到一分钱,就能打倒姚文元?至今我都不明白这些歌谣究竟是何人编出来的。